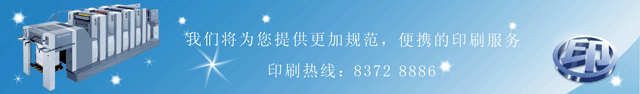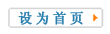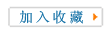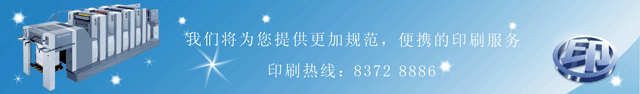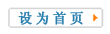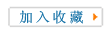|
|
摄影的严肃 严肃的摄影
福州众印网 2006/10/10 21:10:00 来源:转载
《世界当代摄影家告白》 顾铮/编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/出版
在西方,关于摄影的论说与文字,太多太多了——国中献身于当代严肃摄影的边缘人,想必早有自己的作品与识见——这本书,我宁可相信对于国中的画家们,对所有愿意睁开眼睛,用心观看的人,大有裨益。
出于绘画的傲慢与偏见,几十年来,大部分视觉艺术家对视觉艺术的核心问题视而不见。恕我斗胆冒犯:我们的绘画、雕刻、设计、电影、戏剧、电视,甚至包括文学,虽曾试图探究各种尽可能深刻的命题,但因了不同媒材的“工具”意识与不同利益的“行业”藩篱,彼此隔阂,以至彼此无知,恐怕无心触及摄影自诞生迄今而始终关切的严肃命题。
什么命题?为什么那是“严肃”的?我不知道。但这命题一直在那里,高高悬在所有视觉艺术的“头顶”。
每当我面对严肃的摄影,如同遭遇警告,发现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是观看、怎样观看。我积蓄无数理由,为绘画,为绘画残余而可疑的价值辩护,自以为懂得二者的分际,犹如律法,信守如仪。但摄影总能有效地使我暗自动摇,并给我另一副眼睛审视绘画,注视世界——摄影,以其自外于艺术,甚至高于摄影本身的原则——或谓“无原则”——给予我更为宽阔的立场。
但我说不出那是什么立场。关于艺术?关于社会?还是关于“人”?
摄影的专论不曾有教于我。不像绘画、音乐、文学,延绵久长,繁衍了自身的理论,并被包裹其中。摄影没有理论——萨特、福柯、巴特尔、桑塔克,均曾恳切地谈论摄影,周详透辟,视摄影为亟待认知而难以评论的事物。权威摄影评论家亨利·荷曼·史密斯即曾著有专文,题为《批评的困难》。
我没有资格谈论摄影,只是对摄影持续惊讶的人。我甘愿一再迷失于摄影以及关于摄影的文字中。真的,摄影没有理论,如果有,很可能就散布在千差万别的摄影作品与摄影行为中,要么,我们就该倾听这本书中所有摄影家歧义纷呈的真知灼见。
在我们的媒体、美术馆及艺术教育的意识中,“摄影”早已具备,“摄影文化”则尚未真正发生。出版界的情形略微不同,山东画报出版社面向大众的《老照片》系列,若经巴特尔锐眼审视,便得以提出照片背后的大追问。前卫艺术的某一“部位”倒是尖锐地意识到摄影的尖锐,惜乎其中“运动”的成分多于摄影。前时媒体颇为报道了一阵设在平遥的国际摄影展,自然是大好事,不过总觉得像是文艺派对……
摄影的觉醒,应是人的觉醒,我看见,中国的无数表象与隐秘,尚在摄影机前沉睡。
在重要的世界摄影舞台,我常为东瀛小国的摄影深度所震撼。我不妒嫉沃霍尔与杜尚,但难以遏制对日本人的妒嫉:此事非关民族的虚荣与自尊:我们的体育、电影、前卫艺术(包括其中有限的摄影作品)早已“走向世界”,然而在“世界摄影”中,虽然常会出现西方摄影家镜头下的“旧中国”或“新中国”,但恕我直言:罕见,或根本看不见中国摄影家。
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。
摄影比任何艺术更严肃、更无情。摄影难以为社会所驾驭。惟摄影胆敢自外于艺术,如书中大部分摄影家,宁可悬置自己的身份。他们,是一小撮内心深处不顾一切的人。
巴特尔对这本书中格外个人化、风格化,或注重新闻纪实的摄影,均不看重,他有道理。但他洞察摄影的桀骜不驯,竟将摄影认作是“疯狂的姊妹”。他发现,“持续地注视”照片,总伴随着“潜在的疯狂,”因为“注视既受真理影响,也受疯狂左右。”当他在《明室》的书写中寻获摄影的“所思”乃是“此曾在”——较为周全的翻译是:“曾经存在,但现已不存在的东西”——结论是:“摄影、疯狂,与某种不知名的事物有所关联,”那“不知名”的,是什么呢?他称之为人心的“慈悲”: 《世界当代摄影家告白》 顾铮/编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/出版
在西方,关于摄影的论说与文字,太多太多了——国中献身于当代严肃摄影的边缘人,想必早有自己的作品与识见——这本书,我宁可相信对于国中的画家们,对所有愿意睁开眼睛,用心观看的人,大有裨益。
出于绘画的傲慢与偏见,几十年来,大部分视觉艺术家对视觉艺术的核心问题视而不见。恕我斗胆冒犯:我们的绘画、雕刻、设计、电影、戏剧、电视,甚至包括文学,虽曾试图探究各种尽可能深刻的命题,但因了不同媒材的“工具”意识与不同利益的“行业”藩篱,彼此隔阂,以至彼此无知,恐怕无心触及摄影自诞生迄今而始终关切的严肃命题。
什么命题?为什么那是“严肃”的?我不知道。但这命题一直在那里,高高悬在所有视觉艺术的“头顶”。
每当我面对严肃的摄影,如同遭遇警告,发现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是观看、怎样观看。我积蓄无数理由,为绘画,为绘画残余而可疑的价值辩护,自以为懂得二者的分际,犹如律法,信守如仪。但摄影总能有效地使我暗自动摇,并给我另一副眼睛审视绘画,注视世界——摄影,以其自外于艺术,甚至高于摄影本身的原则——或谓“无原则”——给予我更为宽阔的立场。
但我说不出那是什么立场。关于艺术?关于社会?还是关于“人”?
摄影的专论不曾有教于我。不像绘画、音乐、文学,延绵久长,繁衍了自身的理论,并被包裹其中。摄影没有理论——萨特、福柯、巴特尔、桑塔克,均曾恳切地谈论摄影,周详透辟,视摄影为亟待认知而难以评论的事物。权威摄影评论家亨利·荷曼·史密斯即曾著有专文,题为《批评的困难》。
我没有资格谈论摄影,只是对摄影持续惊讶的人。我甘愿一再迷失于摄影以及关于摄影的文字中。真的,摄影没有理论,如果有,很可能就散布在千差万别的摄影作品与摄影行为中,要么,我们就该倾听这本书中所有摄影家歧义纷呈的真知灼见。
在我们的媒体、美术馆及艺术教育的意识中,“摄影”早已具备,“摄影文化”则尚未真正发生。出版界的情形略微不同,山东画报出版社面向大众的《老照片》系列,若经巴特尔锐眼审视,便得以提出照片背后的大追问。前卫艺术的某一“部位”倒是尖锐地意识到摄影的尖锐,惜乎其中“运动”的成分多于摄影。前时媒体颇为报道了一阵设在平遥的国际摄影展,自然是大好事,不过总觉得像是文艺派对……
摄影的觉醒,应是人的觉醒,我看见,中国的无数表象与隐秘,尚在摄影机前沉睡。
在重要的世界摄影舞台,我常为东瀛小国的摄影深度所震撼。我不妒嫉沃霍尔与杜尚,但难以遏制对日本人的妒嫉:此事非关民族的虚荣与自尊:我们的体育、电影、前卫艺术(包括其中有限的摄影作品)早已“走向世界”,然而在“世界摄影”中,虽然常会出现西方摄影家镜头下的“旧中国”或“新中国”,但恕我直言:罕见,或根本看不见中国摄影家。
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。
摄影比任何艺术更严肃、更无情。摄影难以为社会所驾驭。惟摄影胆敢自外于艺术,如书中大部分摄影家,宁可悬置自己的身份。他们,是一小撮内心深处不顾一切的人。
巴特尔对这本书中格外个人化、风格化,或注重新闻纪实的摄影,均不看重,他有道理。但他洞察摄影的桀骜不驯,竟将摄影认作是“疯狂的姊妹”。他发现,“持续地注视”照片,总伴随着“潜在的疯狂,”因为“注视既受真理影响,也受疯狂左右。”当他在《明室》的书写中寻获摄影的“所思”乃是“此曾在”——较为周全的翻译是:“曾经存在,但现已不存在的东西”——结论是:“摄影、疯狂,与某种不知名的事物有所关联,”那“不知名”的,是什么呢?他称之为人心的“慈悲”: “从一张张照片,我……疯狂地步入景中,进入像中,双臂拥抱已逝去或将逝去者,犹如尼采所为:1889年1月3日那天,他投向一匹遭受牺牲的马,抱颈痛哭:因慈悲而发狂。”
在《明室》的末尾,他写道:
“社会致力于安抚摄影,缓和疯狂。因这疯狂不断威胁着照片的观看者……为此,社会有两项预防的途径可采用:第一道途径是将摄影视为一门艺术,因没有任何艺术是疯狂的。摄影家因而一心一意与艺术竞争,甘心接纳绘画的修辞学与其高尚的展览方式。……另一安抚途径是让它大众化、群体化、通俗化……因为普及化的摄影影像,藉展示说明的名义,反而将这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人间给非真实化了。”
摄影的选择是什么:
“疯狂或明智?摄影可为二者之一……让摄影顺从美好梦想的文明化符征,或者,迎对从摄影中醒觉的固执的真实。”
去除了上下文,这些话可能是费解的,我所以反复阅读(台湾译版)的《明室》。他说的是西方——久在西方,我对他的言说始有渐进渐深的认知。中国眼下的进步,已初具他对影像文化所概括的景观:影像正在我们周围泛滥:“艺术”的,或“大众”的。而“从摄影中醒觉固执的真实”,却是稀有的经验,一旦遭遇,仿佛被目光逼视,不免惊怵,以至难堪。摄影犹如言论。在一个诚实的言论尚未获致充分表达的空间,摄影的处境必是暧昧的。摄影家可能并不自知。
我被这本书触动的不是照片,而是言论的锋利。此外,我要说,摄影不应该仅在书页中被观看。目击一幅原版照片,比镜头目击真实更具说服力。凝视原版的质感与尺寸——这质感、尺寸绝不仅指作品的物质层面——是不可取代的观看经验,并从深处影响一个人。
愿伟大的世界摄影直接迎对我们的目光。还要等多久?此刻,我谨感谢顾铮先生坚持多年的编述,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做成这本书。
本文标题:摄影的严肃 严肃的摄影
福州印刷.福州印刷网.福州印刷厂.福州众印网.宣传册印刷.宣传单印刷.包装盒印刷.手提袋印刷.印务公司.光盘印刷.中秋月饼盒包装印刷厂.企业画册印刷.不干胶印刷.无纺布袋印刷
福州印刷、福州印刷网fzysw.com福州专业的纸品印刷厂、福州众印网是超赞的印刷超市
|
|